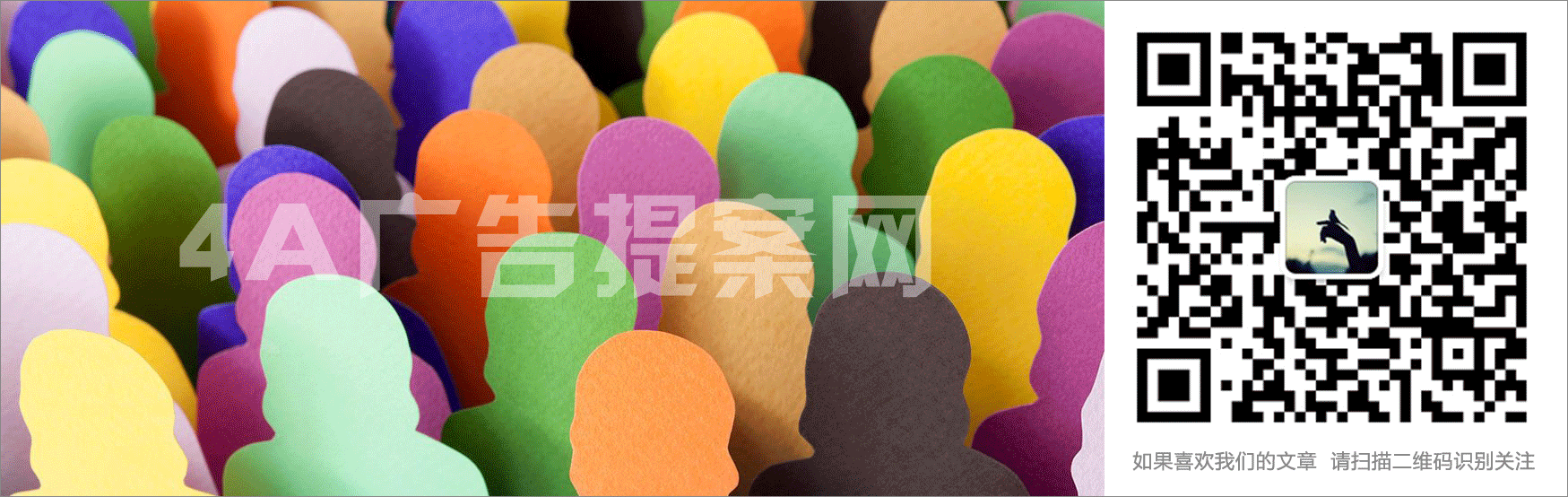导读:不到4年时间,微信月活跃账户达3.96亿。一个人时、聚会时,在车上、在路上,在睡前、在醒来后,人们争分夺秒地刷着“朋友圈”,沉浸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在中国,“微信依赖症”正在形成。这种依赖症背后,是一种孤独的症候。微信有让你变得越来越孤独吗?
被微信“绑架”了
科技宅男爱上了手机里的人工智能系统OS1,跟“她”(由性感女神斯嘉丽·约翰逊配音,相当于iPhone里的Siri)发生了一段人机畸恋,最后发现“她”同时爱上了461人,遂罢用手机,回到不美好但真实的现实生活。以上是最近受热捧电影《她》(Her)的情景,离我们真实世界越来越近。
坐在我面前的曹国钧,男,49岁,是中国一家国企的信息部主任。他手持4个终端,有4个微信私人账号、3万多微友、15个微信公号、2000个微信群。500人以上的大群就有10个。经营这么多微信,与他的日常工作并没有直接关系。
纽约大学社会学家埃里克·兰纳伯格(EricKlinenberg)曾在《大西洋月刊》2012年5月封面文章《Facebook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孤独吗?》中说,社交互动的质量而非数量最能预测孤独状况。他在接受《商业周刊/中文版》采访时,重申了这样的观点。
大卫·梭罗说,社交是廉价的。他独居在瓦尔登湖边,偶尔观察两只蚂蚁在打架,他所描述的是惠特曼时代自然主义的美国。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大卫·里斯曼的学术著作《孤独的人群——美国人性格变动之研究》竟然风靡一时,击中了人们在机器时代的脆弱内心。
现在新机器把整个社会都卷入进来,一种新的社会性格正在形成。在中国,这种社会性格,有一个新名字:微信依赖症。这种依赖症背后,在社会学家们看来,是一种孤独的症候。
依赖症与孤独的关系,用约翰·卡乔波(JohnCacioppo)向《商业周刊/中文版》描述的一个比喻就很容易理解:就像小汽车,如果你开车去见朋友,你会很快乐;如果你一个人驾车看着旁人的狂欢,你就孤独。如果小汽车创造了郊区,它也创造了孤独。卡乔波是芝加哥大学认知和社会神经学中心负责人、孤独专家,多年研究社交媒体。
根据微信官方数据,不到4年时间,微信已积累了8亿用户,超过了欧洲总人口,其中月活跃账户达3.96亿。公众号数量超过了580万,日均增长1.5万。庞大用户的活跃,让微信估值飙升,里昂证券亚洲4个月前在报告中估值,说微信价值已达640亿美元,三倍于Facebook收购的WhatsApp。
微信让许多人患上了这种新病症:微信依赖症。严格说,这是一种社会病灶,一种社会性格和习惯的形成——可能好,也可能坏。
“我真的崩溃了。”回忆起一年前的事儿,曹国钧不停摇头。2013年7月22日,整整一天,曹国钧都抱着手机,不停地点击微信登录按钮。当天上午,由于通信电缆问题,微信大面积崩溃,和数亿受影响的其他微信用户一样,曹国钧无法登录微信。那天,他第一次和他那个由3万多好友组成的庞大微信世界失联,他想知道谁又在约饭局了,哪位微友发了求救信号:比如小孩上学择校、比如找医生什么的。
活在微信这孤独星球上
“社交应用就是为孤独而生的,孤独的人喜欢社交媒体。”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罗兰德·沃金(RonaldDworkin)对《商业周刊/中文版》说。
7月10日下午,我们与曹国钧见面时,他穿着一件草绿色的T恤,就是微信App底色的那种绿。曹国钧把他和家人之间有限的沟通也挪到了微信上。他的手指在iPad屏幕上翻了好几页,才找到他与儿子的聊天记录。征得他本人的同意,我们引用了以下一段对话:
儿子:“底特律,20:38。”
父亲:“能赶到下一班吗?如何安排?”
儿子:“到达芝加哥,当地时间21:03。”
没有一点多余信息。父子之间的对话如果有一些柔情蜜意的问候或许更好。曹国钧还建了一个小群给一家三口。起初,他会在小群里敲一句,“今天不回去了。”现在,他只有在要回家的时候,才在里面说一句“今天回去”。他说妻子也已经习惯了。
接受采访时,曹国钧也不忘滑动微信页面,选择性地点开一些未读信息,歪着头把跟脸大小相当的iPad凑到耳边听语音微信。
这台iPad上,还安装了日本即时通信应用Line、中国电信和网易联合推出的移动IM“易信”、阿里巴巴的“来往”、网络即时语音沟通工具“Skype”、新浪旗下类微信社交IM产品“微米”等。
望着曹国钧与微友们忙得不亦乐乎,我们很难问出口:你孤独吗?这不是梭罗似的孤独,字义一目了然。有了社交媒体和工具,人们非常忙碌地参与了各种社交群组和讨论。1990年代时是邮件组和BBS;之后是QQ和MSN;博客、Twitter、微博、Facebook、Path、Instragram、WhatsApp、陌陌……
“为什么我们花费了很多时间与技术在一起,却吝啬把时间分给现实生活中的人?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这是麻省理工学院社会学家雪莉·特克(SherryTurkle)的疑惑。1990年代初,她沉醉于网络聊天室和在线虚拟社区,写书庆祝网络新生活。20多年后,昔日的科技代言人变身科技反思者。
网络带来了新空间。在这个新兴空间的一端,雪莉·特克采访到在同一张床上给对方发短信或者写电子邮件的夫妻。她在《群体性孤独》一书中对此评论说:手机在身让孩子们有了安全感,但他们生怕漏掉任何一条重要信息。网上友情容易获得,但这种亲密关系存在着随时失去的风险。
微信创始人张小龙从未公开解释微信启动页面的寓意:一个孤独小人独自面对星球。人们乐意把它解读为微信增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帮人解决孤独问题。但张小龙也承认,“通过技术解决不了人的内心情感需求”。
据统计,3000多万美国人独自生活,约占美国家庭总数的四分之一。人们夜以继日地通过手机和电脑保持不间断的联系,社交网络繁忙喧闹,个人却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孤立与疏离。
“社交媒体融入生活,这一切刚刚开始。”埃里克·克兰纳伯格在邮件中对《商业周刊/中文版》说。
我们拥有越来越多的新的社交工具,却越来越少地拥有一个真实的社会。罗兰德·沃金著有《虚拟幸福:新幸福阶层的阴暗面》等书。他发现,在Facebook上人们很难建立强联系(关系)。“那些只是熟人,不是朋友。有的人有超过200个Facebook好友,这实在太疯狂了。你在网上有多少朋友并不能反映现实生活中有多少朋友。”他在电话中说。
科技只是工具
社交网络依赖症让人变得孤独,是危言耸听吗?是社会学家杞人忧天吗?不是说好的“工具无罪”吗?
“社交网络不会让人们感到更孤单。相反,频繁地更新Facebook会减少孤独,因为更新状态勤快的人会感到自己和朋友们联结在一起。”德国社交网络研究学者格罗斯·德特斯(GrosseFenneDeters)在电话中对《商业周刊/中文版》说。她研究了人们使用Facebook的频率如何影响他们看待朋友、家人以及社会的方式。
曹国钧在我们面前展示了他的2部智能手机以及2台iPad,这4部终端设备里都安装了微信。在那台屏幕花掉的iPad上,微信图标很显眼,曹国钧点开微信应用,左下角的微信未读数字一直在跳转、增加,最后停在了314772。
如果曹国钧每一秒看一条信息,这需要87.4个小时。如果他还回复一些信息,估计要花更多时间,这还不算在他看信息同时,又跳出的无数信息。
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拉诺维特(MarkGranovetter)从互动的频率、感情力量、亲密程度和互惠交换四个维度,把联结分为强弱两种。
“我知道很多人担忧网络社交会使人孤独,他们害怕网络交往会成为现实社交的替代品。但更多研究认为,这种担心是不正确的,因为科技只是工具,会带来什么结果完全取决于人怎么用它。很有可能是,人因为孤独了,才跑去网络上找人交流。”格罗斯·德特斯说。
约翰·卡乔波也支持格罗斯·德特斯的观点。他在《孤独是可耻的:人性与社会联系的需求》一书中将孤独比喻成“饥饿”,它们是某种信号,预警你饿了或缺爱了。
卡乔波基于大量的社会学调查、生物学与流行病学研究,提出了一个“孤独模型”。他发现,一个人是否孤独,并不能根据Ta的联系人多少做出判断。许多人拥有很多“她”,但仍然很孤独。
电影《她》男主角的工作是在漂亮的手写信网站上替别人写情书。他自己经历婚姻破碎,面临中年危机;他负责传递情感,跟有好感的女同事却有表达障碍;他享受指尖运动和虚拟性爱,却在洛杉矶的街头一个人游荡,倍感孤独……
“微信孤独症”五大症状
如果说存在“微信孤独症”,典型的症状有哪些?那么人使用微信等移动社交工具,个体感受是否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普遍性?
今年4月,一条关于社交狂人的视频在网络上被播放了将近4500万次。“我有422个联系人,但我很孤独……”一位叫加里·特克(GaryTurk)的年轻人面对镜头,控诉手机加重了人的孤独。
视频中是我们日常中司空见惯的画面:几位年轻人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各自低头滑动手机屏幕;繁华的街道上,人潮人海中,一个男人停步低头玩手机;屋子里,一个小孩儿目不转睛地玩iPad游戏,留下屋外空荡荡的秋千。“我们假装没有感觉到社交孤立。”加里·特克说。
曹国钧平时大部分时间沉浸在微信的虚拟世界里,睡觉除外。他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躺在床上看微信。早上开车上班路上,堵车时刷微信,等红绿灯时也看微信,分秒必争。
白天,他所有碎片化的时间都用在了微信上,晚上下班,还有一堆微信公众账号等着他打理。他主动在群里发起话题,引导讨论,以维护群的活跃度;他给发小广告、收集联系方式的微友“黄牌”或“红牌”,维护群的秩序;他翻看认识的不认识的人发来的看不完的微信消息,迎来送往……
埃里克·兰纳伯格说,“每个时代人们都会感到焦虑,但这种焦虑常常伴随新的沟通技术出现。”对于微信社交逐渐呈现出重度依赖现象,我们又提炼出“微信孤独症”五大症状:
症状一:我们已经被微信“绑架”了,我们的生活就是:微信见。
一个网络段子:“每天早晨,人类从微信中醒来,不刷牙、不洗脸、不下床……第一件事,用各种各样的安卓、iOS、iPhone、iPad、三星、HTC、联想、OPPO……奔向同一个App:微信。每天早晨,每个草根和屌丝,都突然找到了皇帝批奏折的感觉,要浏览比真皇帝的奏折还要多得多的微信留言。”
新媒体观察者、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师魏武挥也是个微信重度用户,几乎从不退出微信。他说,“和弱关系相处久了,就会导致不会处理强关系。现在微信的用户很多都很年轻,他们不擅长处理强关系,与父母的关系不像上一辈那么密切。”
过度频繁的联系让人产生习惯性的心理饥饿感,“总担心错过什么,总担心失去什么。”DCCI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说,“我们联系别人不仅是为了减少焦虑,也是在追求一种存在感。”
刘兴亮已经离不开微信了。“PC时代的社交有在线和不在线两个状态,移动互联网时代默认随时随地永远在线。我们发出一条微信,默认对方立刻能收到。”
很多人对微信态度复杂:既严重依赖,又不堪其扰;既有错过的焦虑感,又有病态的强迫症。
这是新时代的迷幻药:你已经上瘾了,欲罢不能。“有时候挺讨厌这个东西的。比如不想被打扰的时候,它还叭叭叭响。”魏武挥说。
症状二:在微信上你知道对方不是一条狗,但你们是熟悉的陌生人。
刘兴亮发现,“社交工具让网友变成了朋友,也让朋友变成了网友。”他和一位好哥们儿同在北京,一个住东边,一个住西边,30km的现实距离难以跨越,一年见不了几次面。但他们常在微信老乡群、同学群中聊聊天,通过彼此的朋友圈了解对方的动态。“朋友就变成了网友,这时候就孤独了。”
2005年,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社会数量研究所所长诺曼·尼(NormanNie)对4113名互联网使用者进行调查后,在《斯坦福报告》中说:“人们在网上待的时间越长,在现实中与人打交道的机会就越少。”科技正促成一些“后现代主义时代的家庭”。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每人待在各自的房间上网。陌生人社交App陌陌CEO唐岩认为,家庭成员的关系变得疏离,也许是社会的组织结构变了。“以前,家庭对人非常重要,基本上血缘关系决定了你在社会上能获得的帮助;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你的同事、朋友在你生活中占的比重往往要超过家人。人最容易产生一种偷懒的思维方式就是:哎呀,人心不古,这个社会变了。”
症状三:微信已经成了一种新的身份ID,但你从此进入了一个美丽新世界吗?
套用“垮掉的一代”诗人艾伦·金斯伯格的诗句:“我看到这一代精英,一个个毁于微信……”刘兴亮有3000多个微信联系人,4000多个手机联系人,常联系的不到200个。他不是没想过控制联系人的数量,但他发现每参加一场活动,添加微信号、扫微信二维码成了标准动作,传统的名片退居二线。不过,“我觉得微信在线的时候很热闹,不在线的时候很孤独。”
2014年7月5日,微信官方公布了微信群升级的新规则:人数允许超100人,但被邀请入超过100人群的微信好友必须是已开通微信支付的用户。商业化野心昭然若揭。
症状四:如果说微博像信息集市、大字报,微信朋友圈更像树洞、情绪反射器。梦想没照进现实,内心有很多阴暗角落。
在微信朋友圈中,爱猫的秀猫,媒体人爱黑媒体业自身,秀恩爱晒寂寞的也大有人在。上传图片,你可以使用“群组”功能来选择看你的人。“群组”所藏的秘密也很多,从“密友最爱”到“无公害”,再到“不太熟”,亲疏关系非常明显。
有位微信典型用户,女孩蕊蕊需要正能量才能开始新的一天,她几乎每天清早都会在朋友圈里发“早安”系列的心灵鸡汤。有天早晨,一位朋友留言,“我还以为是系统自动发的呢。”
症状五:马化腾的“连接一切”野心很大,但最终人会被机器所控制吗?
曹国钧到哪里都要带着4台移动终端,里面的微信是他连接世界的密匙。这像《黑客帝国》里人的脑袋后面插着电脑线的场景吗?
2013年11月,腾讯董事长马化腾在“W3C大会”上,把“连接一切”作为通向互联网未来的七个路标的第一个路标。“智能手机成为人的一个电子器官的延伸这个特征越来越明显,它有摄像头、有感应器,而且通过互联网连在一起了。”腾讯微信团队拒绝对社交孤独话题发表评论。
从来都有人赞美、神话科技,也不乏有人反科技。《你并非机器》的作者杰伦·拉尼尔(JaronLanier)担心人变得去适应机器和科技。
互联网专家、财讯传媒集团首席战略官段永朝是科技的追随者。他最近在手腕上拴了一个可以记录运动量、睡眠质量等健康信息的Fitbit智能手环,“我想每天24小时拴着它,拴上几个月,看我的认知心理能否带来改变。”他坚信人与科技注定彼此交融。科幻小说和电影老提到机器人统治世界。
“人的孤独感和对科技发展的担忧,都源于对确定性和秩序的失去的恐惧。”段永朝说,“人是万物的灵长。莎士比亚这句话简直就是文艺复兴以来对人的情感的高度概括。人居于世界中央的思想延续了500多年,当人发现自己有可能丧失万物灵长的位置,这个世界可能逃脱我们的手心,能不焦虑吗?”段永朝反问。
熟人,还是朋友?
“当我们哭泣时,需要的是一个肩膀,而不是一条信息。”英国牛津大学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Dunbar)接受《商业周刊/中文版》邮件采访时,如此形象地描述社交网络与人的关系。
曹国钧每天收到微信无数,但未读微信数字也大得惊人,所有的人都是朋友,又都不是朋友。
在电影《她》中,有一次,男主角的人工智能助手毫无预兆地消失了,他恐慌至极。
邓巴20多年前提出的著名的“邓巴数字”,即“150定律”(RuleOf150),在移动社交时代仍然有效。“150人似乎是我们能够建立社交关系的人数上限,在这种关系中,我们了解他们是谁,以及与我们的关系。”社交AppPath就采用了邓巴理论,设定每个用户最多拥有150名好友。
大脑皮层越大,它们所能应付的群体规模也就越大。该定律根据猿猴的智力与社交网络推断,人类智力将允许人类拥有稳定社交网络的人数是147.8人,四舍五入大约是150人。这便是1992年,邓巴发表在《人类进化》杂志上的研究成果。
邓巴理论与国内社交表现不太相符。微博微信们的好友动辄数百人,达500人的微信大群也正在扩充。Twitter用户经常互动的好友人数平均在100到200人之间。Facebook允许用户拥有5000名好友,但平均好友人数为190人——略高于150人。邓巴认为这属于误差范围之内。“友情是有深浅的。Facebook让你加一些现实世界不在你身边的人(这些人我更愿意称为熟人而不是朋友),他们会加比150个人多350来让社交圈变成500。”
《彭博商业周刊》2013年写过《人类逃不出邓巴数:洞察人类的社交密码》,“就像人类无法在水下呼吸、两秒半内跑不完百米、用肉眼看不到微波,大多数人最多只能与150人建立起实质关系,不可能比这个数字多出太多。从认知角度来讲,我们的大脑天生就不具备这样的功能。一旦一个群体的人数超过150人,成员之间的关系就开始淡化……邓巴理论解释的是限制,而正是限制造就了伟大的架构和伟大的公司。”
邓巴实际上给出的是数字范畴,最核心的圈子可能有三五人,是最亲密的朋友;然后是12到15人;然后是50人。邓巴在《你需要多少朋友?》一书中写道:“50人通常是大洋洲和非洲土著居民等狩猎采集型社会中集体在外过夜的人数规模。”
罗宾·邓巴不用社交媒体,手机只用来打电话、发短信,而且只联系那些日常生活中他常常能见到的人。“线上的社交关系只有通过线下的会面才能存活,人们总把随便的熟人关系误以为是真正的友情。”
既然不是社交数量而是质量影响人的孤独状态,永远在线带来的是随时被干扰、被强迫,那么,我们这个时代的公司和用户都应该反思一下技术伦理及异化问题了。
约翰·卡乔波说,互联网只允许虚假的亲密。在《孤独是可耻的》中,他描述了孤独泛滥给人类健康带来的深远影响。“养宠物,结交网上朋友,是天生群居动物为了满足强制需求所做的可贵尝试,但是替代物永远无法弥补真品。”“真品”是指有血有肉的人。
《她》获第86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剧本奖,结局以女OS1的离去结尾,留下宅男面对孤独的真实人生。而曹国钧无法想象没有微信的日子。
来源: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周琼媛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4A广告提案网 | 广告小报 | 广告圈那点事 » 微信依赖症背后:孤独的中国人
 4A广告提案网 | 广告小报 | 广告圈那点事
4A广告提案网 | 广告小报 | 广告圈那点事